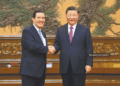圖文:張銘隆
再來一則絕對使人怨妒的異類接觸:
這一隻小小鳥只比綠繡眼大一點點,羽色也有點相像,如果牠停得稍遠一點或是在樹上和綠繡眼混群,我會說「這隻綠繡眼吃得太胖了」;可是牠絕不是綠繡眼,因為牠是白色眼線,不是綠繡眼的白眼眶。
小小鳥從下午就開始船頭船尾的流連,各處纜繩、電線上都曾落腳,但就是不曾落到甲板面上(這點倒和青笛仔蠻像的)。
午後不久,我從前甲板回到艙房,眼角感覺有一飛影穿門而去。再稍晚,躺在床上看書的我忽然覺得床頭邊有東西在動,本來艙間到處都是蟑螂,小桌上有東西在動並不奇怪,可是定睛一看,原來是這隻小傢伙,落在我床頭邊的塑膠櫃上,半個身體被書本遮住,只看到一個小小鳥頭在橫置的保特瓶上一啄一啄的很是可愛,一會兒,牠也發現我在看牠了,牠一邊斜睨著我,一邊還是啄著啄著瓶裡那看得到喝不到的飲水。
我直覺得好奇: 這樣一隻陸生樹棲(從牠的飛行和停歇方式研判)的野鳥,怎麼會知道保特瓶裡的清水可以飲用?怎麼會知道外邊那一片汪洋的海水不可飲用? 我以前划獨木舟出海時曾看見浮在海面上短暫水浴後再起飛的鴿子,也曾救過落海後無法再飛起的鴿子。可是這樣連甲板面都不太肯落腳的小小鳥,我可以確定牠不是海鳥,應不可能漂浮在海面上休息。
我們的船位離最近的彭佳嶼25浬,最近的大島岸線是鼻頭角距離45浬,牠不知道多久沒喝到清水了? 牠的行為就像「小蟻雄兵」卡通影片中那隻會思考的小蟻一樣:這透明的塑膠膜是一層難以破解的力場? 真想為牠打開保特瓶,請牠暢飲……。
可是我知道我如果動作稍微大一點,一定會嚇得牠飛走,又想,外甲板上有一桶船員們洗手的清水,牠應該找得到、喝得到的。想著想著,這樣看著牠啄著水瓶約有一分鐘,牠可能見我不肯給水,就倏地飛走了。
這一天的甲板作業到午夜後才泊錨休息,凌晨三點多,我內急醒來,忽然發現牠就棲停在離我伸手可及的電線上,小腦袋縮藏在膨鬆著的羽毛下,比黃鶺鴒更不足一握的嬌小身形,令人更生憐愛心情。
我悄悄地從臥舖上下來,往床尾摸出相機,為牠拍了幾張微距的睡姿相片,燈暗船搖也不知拍得如何,但是看牠細緻羽毛令人禁不住用左手指尖輕觸了一下翼尖;結果牠睡眼惺忪地動了一下,彷彿夢囈:「哇金愛睏,嘜吵啦!」。
真也捨不得吵醒牠,換了頭重新睡下。天亮時,看牠不知何時已離去,就這樣結束了幾分聊齋和完全單戀的一夜情。

圖說:
從聊齋中現身的鳥仙,就停棲在風扇的電線上。
驚喜邂逅的親密距離,近得教人不敢相信。
滿臉惺忪的模糊照片,經鳥友協助辨識應是「極北柳鶯」。
漂鳥曾經落腳的床頭,左下角是曾引動牠興趣的瓶裝水。